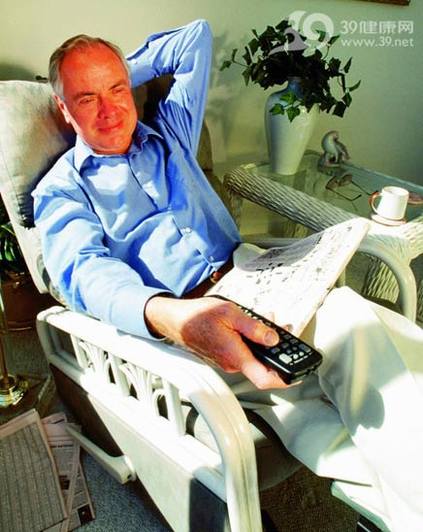
怕爸爸摔倒,所以我们常常与爸爸面对面地站着,一手扶住他的腰,另一手架住他不能动的那半边肩膀,而爸爸则用他能活动的那只手扶住我们的肩。那样子,叫人感觉像一对共舞的人。
就这样,我们常常扶着爸爸,一步一步向后退;爸爸依靠着我们,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。这个时候,总是感觉仿佛是我们在扶着爸爸跳着慢四—没有音乐,我们踩着心的音律,在屋子里慢慢地旋来旋去。
这个时候的爸爸,心情一般都挺好,我们常常边走边聊。有的时候,为了训练爸爸的反应能力,我们就要爸爸边走边从一百倒数到一,或是让爸爸一人从头倒数到尾,或是我们与爸爸一人倒数一组数字;有的时候,为了训练爸爸的口齿,我们就教爸爸读汉语拼音,我们读一遍,然后让爸爸大声地跟读一遍;最多的时候,是我们边扶着爸爸倒走,边给爸爸讲白日里的所见所闻,爸爸大多数时候则微笑着专注地看着我们;心情最好的时候,爸爸会一边走,一边唱他最喜欢唱的《草原之夜》、《乌苏里船歌》……我们则微笑着看着他,和着他的歌声,带着他慢移慢舞……那时候,是感觉与爸爸最亲近的时候。
一日,与同事闲谈,说起了扶爸爸走路的感觉,就好像是在扶着爸爸跳慢四。同事略微一顿,微笑着说了一句话:“等到什么时候你可以扶着你爸爸跳快三的时候,你爸爸就会好了。”
仿佛一语惊醒梦中人,那一刻的我一下子痴了。
从那以后,再扶爸爸走路的时候,总是下意识地稍稍加快一点步子—期待着能扶爸爸跳快三的那一天!期待着爸爸好起来的那一天!
父亲的泥脚白帆
碎石路上,荆棘满地。父亲光着脚,健步如飞,我提着一双蓝色的鞋,拼命地追赶却怎么也追不上,一丛树枝绊住,我跌倒了,父亲更远了,我声嘶力竭地喊:
“爸爸,您的鞋……”
然后是梦醒。每一次,母亲都告诉我,父亲是从不穿鞋的。
是的,父亲是不穿鞋的,像许多农民那样,厚厚的脚板,粗糙的脚趾,踩着田埂春种秋收;沿着山径去伐薪砍柴;从早到晚,从春到秋—那沾满泥水的脚,永远是那么灵巧自如。
小时候,看着父亲不穿鞋的样子,觉得洒脱自然。上街购物,父亲走在皮鞋、胶鞋的队伍中,步伐是那样稳健;带我上学,父亲那滴着泥水的双脚,在光洁的石板路上留下湿湿的脚印,我跟着父亲那粗大的脚印走路,觉得又平稳又安全。
也许后来看多了穿鞋的人,也许是虚荣心作祟,渐渐地,我觉得赤脚又土又难看,甚至有些粗野。于是对父亲就有些不满,拒绝他带我去学校。高中住校后,每隔一段时间,父亲总会来看我,每一次看到父亲带着泥土的脚,喜悦和想念都变为不快和烦恼。
一个初春的黄昏,父亲又到学校来。我一眼看见他那双沾满污泥的脚,又气又急,对父亲大声嚷道:“以后您不要光着脚到学校来好吗?”父亲静默了一会儿,笑笑,从帆布袋里拿出一包花生,又从口袋里掏出40元钱塞在我手里。“拿去,好好照顾自己,天晚了,我还得赶回家。”说完,转过身,挑起担走了。父亲的背已微驼,步履有些迟缓蹒跚,再不似以前那样健壮有力。
再一次来看我时,父亲的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蓝布鞋。
“你看,这双鞋好不好看!”
父亲喜悦的神情,掩不住地兴奋,竟使我十分茫然,恍若失去了什么。后来,母亲告诉我,穿着鞋回家的父亲,脚跟与脚趾打起了泡,几天不能走路。我的心在滴血。
去年,我上了大学。启程北上那天,父亲光着脚,担着母亲陪嫁时的那只旧皮箱,送我上县城搭车,依然如从前一样健步如飞—那一幕,我终身难忘。
去年冬天,小弟来信说,父亲病了。闻讯后,我心急如焚,好不容易熬到最后一门考完,我急不可耐地踏上归程。当我到家的时候,正赶上父亲出院回家。出院后的父亲,更加憔悴了,走路得拄拐杖,还须搀扶。我不禁想起了一句犹太谚语:“父亲帮助儿子时,两人都笑了;儿子帮助父亲时,两人都哭了。”可我俩都没有哭,我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我的父亲。
那天夜里,我做了一个梦:大学毕业典礼上,我走上台去领奖,向大家致谢,掌声四起,我泪眼模糊地望着台前的家长席,在冠盖云集、西装革履的人中,有一双敦厚黝黑的泥脚,踏着鲜红的地毯向我走来……
